当我们把勃拉姆斯的作品看作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也同样适用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受“热烈的客观主义”所启发。正是这个客观主义让他能够在这个开始衰落和瓦解的时代仍保持真我。他的同时代人并不让他轻易这样做。他天生缺乏自信并且沉默寡语,他发现能够对付蛮横指责的唯一方法就是他自己的粗鲁行为。他过度的粗鲁举止逐渐为人所知,其原因在于对自由和独立的无边渴望。同时他也乐于接受忠诚交往以及天才朋友陪伴带来的欢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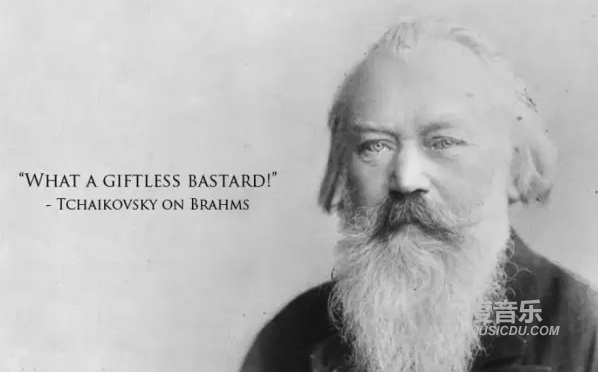
实际上,那些他身边的人常说他的怪癖和无耻的自私都是深深根植于他晚年对这个世界以及他的同辈人(也就是参与“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的蔑视。同时他也意识到,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在日常生活的实际事物中又脱离不了他们。所以当偶尔他不蔑视和粗鲁的时候,他也会以一种带讥讽的机警去应付他们,虽然这些人常常后来才发现甚至从不发现他是多么的机警。有无数关于他的趣闻,尤其是来自维也纳的,值得我们收集和编排我们认为今天仍然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绝大部分的同时代人没有或不能认识到他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心智和精神上是多么的超凡。确实,他没有瓦格纳那种强烈的压倒一切的个人魅力。但是他清晰的视野和理解力,他对生活的责任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和多例子可以说明。理查·斯特劳斯回忆到,当他向勃拉姆斯展示他早年的D小调交响曲时,勃拉姆斯说:“所有这些进出主题之间让音乐连成连续整体的对位都不好。更加有用和必要,同时也是更加难的是学习如何写简单的八小节乐段。”在我的记忆中,理查·斯特劳斯告诉我这件事,并未加任何评论。当然,勃拉姆斯也不能预计到理查·斯特劳斯音乐中发生的巨大发展。抛开这个不谈,他不正正是指出整个音乐发展的最大威胁么?有关勃拉姆斯和他同时代人的整个话题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素材。我非常赞赏他对身边所有人的直率和真诚。当向他提问题时,他的责任感使他从不回避回答,或是给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但这种直率也让他有了一些最有权势和最顽固的敌人。这使人怀疑他是否有必要表现得像尼才或雨果·沃尔夫般无情的直率。
勃拉姆斯的厌恶公开表达自己、完全缺乏社交技巧、加上我之前提到的“热烈的客观主义”,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同样表现出来。他需要独立和果断,这不允许他为一些琐碎事所烦扰,使他生活不显眼,几乎是离群索居。当然,这种行为会常常被误解。当他宣称他从未从他的作品中享受欢娱时(如果真的如此,他不会再写什么东西了),有些人真的相信了。当他假装把他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和切鲁比尼(Cherubini)相比较时,他们也相信了。他习惯于征求好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像克拉拉·舒曼和伊丽莎白·冯·赫索根伯格)对他的作品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错误解读了这些信息,他们就会天真地为他提供意见,他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未被认真对待。
实际上,他任何时候都讨厌讨论他的作品。